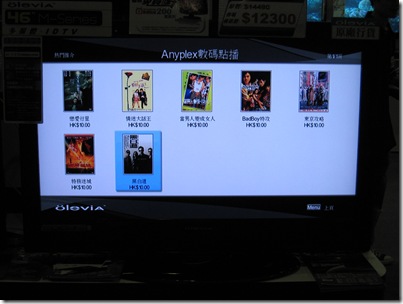有了問題,才有此貼文。我的第一篇米蘭昆德拉,在一個微寒冬夜,抱著不願在大學電腦室捱通宵的決心,躲在校園一角通宵閱讀,可想而知囫圇吞棗的結果是消化不良。
那是《笑忘書》,都付談笑中,便忘了。
後來捧讀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,睡前一讀,真的不能承受,卻又享受如此折磨。
直至讀了作家陳寧在今期《讀書好》的文章,「為何還要讀昆德拉」,是的,要用自身對抗官方的遺忘--「偏偏是在這樣的時候,我們需要繼續閱讀昆德拉。為天安門廣場上的亡魂,為劉曉波,為胡佳,為譚作人,為說不出名字的,為說得出名字的,為我們,為我們的下一代。」
《讀書好》 「為何還要讀昆德拉」 文:陳寧
諾貝爾文學獎可算是國際文壇至高榮譽,每年得獎名單公布前夕,總有諸多猜測或熱門人選。如果問,當今最該得而又未得的作家是誰,最炙手可熱的名字,東方代表是村上春樹,西方可算是米蘭‧昆德拉。不約而同,兩人都在八十年代走紅,前者憑《挪威的森林》奠定日本文學新舵手地位,後者的代表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則風靡一代文藝熱血青年。但分別是,村上春樹才過60歲,寫作生命還在燃燒階段,長寫長有,長跑下去或者真會摘下桂冠;而老昆已行年八十,近年鮮有長篇小說作品,反而較多評論與藝術散文,被認為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。
作為一個擁有特殊政治身份(從鐵幕捷克流亡至法國巴黎)的寫作者,他的異議性與話題性,在八十年代末達至高峰,他獲頒諾獎的最佳時機,已然過去。當共黨倒台,故鄉也加入歐盟,流亡不再必要,他要反對的敵人似乎已經消失,他變成像唐吉訶德那樣的人物,對着某種過去的權力幻象嘮嘮叨叨,盲目放箭,像個可悲又可憐的過氣戰士,活生生是他所書寫的玩笑。在部分對他嗤之以鼻的西方評論家心中,昆德拉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,在法國文壇也沒受到特別厚待。可是,每當他的書出版,卻總會成為話題,攀上法國書店的暢銷書榜,尤其他去國後已改用法文寫作,在法國境內仍是受讀者愛戴的作家。
先把話說在前頭,我也是一個追隨昆德拉多年的讀者,他有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也不會改變這樣的閱讀習慣。
發掘隱世高人
《相遇》是他最新出版的評論集,談他喜歡的文學、藝術與音樂,仍舊是老昆的個人品味。他喜歡的藝術家,總是那些驚世駭俗,卻多多少少給世俗忽視(或不夠重視)的,他就冷冷而篤定地指出這些珍寶,像發掘隱世高人一樣,重新找到珍貴的美學價值。如果不是對藝術有同等的熱情與喜愛,很難追得上他的步伐,但追上去了,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幽微觀察與藝術品味:不夠好的絕對得不到他的歡心。
其中對於小說的藝術,貫徹他向來的偏好,著墨極多。又可見昆德拉仍是熱愛經典,對嚴肅大部頭巨著孜孜不倦,引其作者為同道人。他為小說守門,嚴加掌管着這行業的神聖門檻,把雜質拒諸門外,並為傑作封聖。
而《相遇》裏最動人的章節,我覺得卻是關於他方與鄉愁的書寫。尤其他寫他對奧斯卡‧米沃什的<十一月交響曲>的深透看法以致不惜反對紀德對此詩的漠然並作出最深情的捍衛:「就讓我們把紀德的拒絕當成某種高貴的作法,為的是保護一個異鄉人不容侵犯的孤寂;一個永遠的異鄉人。」(頁136)這樣的昆德拉並不常見,然而正是這樣的昆德拉,才令人尊敬(如不說同情):一個永遠的異鄉人。
便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,閱讀昆德拉更像是一種出於鄉愁的需要。不,不是懷念看似永無止境的冷戰時代,而是懷念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底下的「抗爭精神」。時代的意義,正在於此。為了反抗遺忘,書寫是一種抵抗。所有的異議聲音,成為時代的背景音樂。那是自由大於一切的年代,那是愛情裏充滿背叛與失落的年代,那是不可能談論忠誠與信念的年代。
時代發展下去,當年的敵人似乎瞬間消逝,自由好似輕易可及。於是昆德拉變得過時,變得不合時宜,變得可笑。就像舊廣場上的列寧像,成為被嘲弄的小丑,早已在人民的日常記憶裏給搗碎千萬次。
抵抗遺忘的方法
偏偏是在這樣的時候,我們需要繼續閱讀昆德拉。為天安門廣場上的亡魂,為劉曉波,為胡佳,為譚作人,為說不出名字的,為說得出名字的,為我們,為我們的下一代。戰場沒有消失,只是改變了位置。昆德拉文集近年在中國內地大量給翻譯並被接受,說明新中國憤青還是在他的文字裏找到共鳴。或可說,方法。就是抵抗遺忘的方法。必須言說,與書寫,用己身的紀念來對抗官方的遺忘。
即使今時今日重讀名作如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、《笑忘書》、《生活在他方》、《無知》等,都可再次印證某些命題的輪迴不息,在時代中不曾泯滅。經典是甚麼,照卡爾維諾的說法,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。要經得起時間考驗,就必須看穿時間的偽裝性與歷史的虛假。昆德拉所書寫的,超越一切政治寓言,直達核心:人在權力面前的無力感、命運的必然與偶然、存在的輕與重、流放。這些困擾着現代人的思考,從來沒有過時。只是因應不同場景,換上不同外衣。
而如今讀着昆德拉對於「異鄉人」身份的感懷,更覺切身:雖然在法國以法文寫作,但他像個永遠的局外人。故鄉卻也不再是昔日的故鄉,回歸再無意義亦無必要。在這兩難之地,他永遠生活在他方。
香港人照說也處在這樣的夾縫中,既已回歸祖國卻也不盡是中國的一份子,經濟上依存但政治意念卻不能認同,一種身在故鄉心在他方的曖昧情境,將是揮之不去的身份困惑。
昆德拉與其他藝術家的「相遇」,啟發了他的思考與影響了他的書寫。與昆德拉的相遇,此時此地,也有感慨。